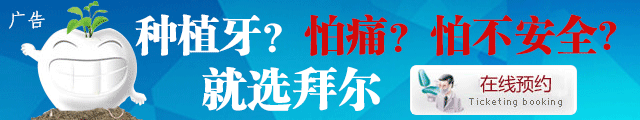西溪之桥下:繁华之地的人文往事
核心提示:受西溪的滋养,桥下镇自古物阜民丰,文化遗存众多,既有以武术之乡著称的瓯渠,也有以枇杷之乡闻名的上湖,还有桥下镇的韩埠老街,曾经商贾云集,繁盛一时。


温州网讯 总长32.5公里的西溪,大部分流经永嘉桥下。受西溪的滋养,桥下镇自古物阜民丰,文化遗存众多,既有以武术之乡著称的瓯渠,也有以枇杷之乡闻名的上湖,还有桥下镇的韩埠老街,曾经商贾云集,繁盛一时。
瓯渠武术,
造就了一批仁人志士
走进瓯渠村,村里蜿蜒穿行着一条溪水,当地人叫瓯渠溪,是西溪最大的支流。刚刚下过暴雨,溪水暴涨,訇訇作响。
出身瓯渠武术世家的吴守武接待了我。他说:瓯渠村初建于南宋淳公式二年(1242年),为吴姓人聚居之地。其吴氏始祖金明公,仙居厚仁里(今白塔镇厚仁)人,幼年好学,文武兼修,遨游东瓯,慕名永嘉山水之秀,徙居瓯渠龙井基,过着隐逸的生活,耕读传家,习武自娱,成为瓯渠的武术始祖。
瓯渠村还散落着一些古民居,居住着老人,说起武术或南拳,他们的话就多了。老人们说:瓯渠地方偏僻,山路险峻,草木幽深,祖辈们出于健身和自卫,习武成风,世代相传,但都内敛而低调,使枪弄棒,不声不响地进行,否则,给官府知道,不抓了才怪呢。瓯渠人称武术为“柴”,这是暗语,谁会弄刀舞棒,就说谁“会几路柴”。建村700多年来,习武从未间断,到了清朝,瓯渠武术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远近闻名的武术世家。
老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清同治年间,瓯渠例贡生吴通辉和他的长子吴承球、次子吴承玕。吴通辉为招武大夫,在瓯渠兴办武书院,传授武术,他的儿子吴承球和吴承玕在1868年双双考取武生员。1873年,兄弟俩又到杭州考武举人,吴承玕上了榜。吴承球人称“球相”,平生擅长梅花柴、七虎拳与八卦掌,尤其擅长轻功,能捕鼠雀,有“猫儿擂”绝招。吴承玕1874年供职兵部四品官员,获赐“青龙偃月刀”一把,重120斤,因长得魁梧,挥舞起大刀虎虎生威。吴承玕在京城广结武林高手,切磋武艺,拳棒刀枪和骑术样样精通。吴承玕还与瑞安文人大学士孙诒让、孙诒泽兄弟相交甚密。
据吴守武介绍,吴承玕供职兵部时间并不长,不满朝廷腐败无能,辞官后居住在平湖市乍浦镇,开设“吴源来号”商行,经商行医,并在温州建立会馆,由次子吴恩侯打理。吴恩侯拳棒弓刀剑样样俱优,在伤科方面很有研究。他还编写了骨伤书籍、武术图谱。
我们在瓯渠村里游走,见到了一栋与众不同的房子,是三间三层的石头房,四面开设小窗,像一座炮楼,房子上还有多处枪眼,与周围钢筋水泥楼房或古旧木质老宅相映衬,显得很是另类。房子前立有石碑,得知是吴超征烈士楼。这栋石头房坐北朝南,在民国初期由吴恩侯兄弟三人出资所建,俗称三间楼,是吴超征年少时的活动场所。
在瓯渠村,无人不晓“上新屋”,这是吴超征的故居。在故居里,我们看到了用鹅卵石铺成精美图案的通道,折射出吴家家道的殷实;看到许多幅传达耕读文化的对联,透露出主人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情怀;看到了布满岁月风尘的石锁刀棍,显示武术世家所特有的一股英雄气质;看到了吴超征东征北伐的图片介绍,知道他坚毅的额头一直撞着粗糙的历史。
我细细阅读吴超征的生平介绍,他出生于1905年,少年时习文练武。1924年被父亲吴恩侯送去参军,考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军事。1925年5月,英日军队镇压在上海游行的工人引发了五卅惨案,黄埔军校学生参与游行示威,在广州沙基遭到英法军队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亡多人,游行队伍中的吴超征幸免于难。
吴守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吴超征在读黄埔军校时,有一次学生们在操场上练习骑术,蒋介石也在场。一匹烈马跑在操场上,一个又一个学生爬上马背都被甩了下来。蒋介石说:哪位同学可以驾驭这匹马,我就把这马送给他。吴超征愿意一试,他勇敢果断,动作十分娴熟地骑到了马背上,骑马姿势英武自信、灵活机敏。蒋介石大加赞赏,非常看重他。
吴超征就是吴守武的爷爷。吴超征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任职,在惠州、长沙、汉口、汉阳、武昌等地作战过,战功卓越,获得“北伐功勋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超征上书请缨,要求征战,奉电召归队,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二师六旅十一团副团长。1933年,日军侵入华北,占领热河。十七军二师奉命据守长城古北口南天门等要隘。4月22日拂晓,八道楼子被日军攻陷,吴超征率军浴血苦战,壮烈殉国,时年29岁。
我没有在故居里看到吴超征征战沙场的形象,但完全可以想象他的英勇与善战。然而,这位抗日英雄的赫赫战功,却曾经长时间被埋没。吴守武说:“文革”中,因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将领,我家被抄,连地板都被撬了,我爷爷留下的许多东西都被抄走,很多名人题词和挽联不知所踪。直到1990年,在吴超征牺牲57年后,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现在,故居里摆放了一些回归的遗物,向后人诉说那些血雨腥风的记忆。
我在瓯渠采访时,与几位年轻人说起吴超征的故事,他们说:故事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爱乡爱国之心在瓯渠村留了下来,瓯渠的武术后继有人。这些年,村里成立了瓯渠武术馆、瓯渠上新屋瓯林拳坛、瓯渠武术协会、瓯渠武术交流中心等,还设立了瓯渠民俗馆,陈列爱乡爱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人,不忘先人业绩。
从瓯渠村出来,已是傍晚,风雨都已停止,四周的青山云雾缭绕,我突然觉得这个村落原来是那么静谧悠然,安宁祥和。而瓯渠溪水仍然是一股摧枯拉朽的气势,扩张的脚步一刻也不停息,一路狂奔,出了前面的山门,便汇到西溪干流之中。
上湖枇杷
清朝时就已名声在外
西溪在峡谷岩壑间百折东流,两岸的荒草野树蓊郁青葱,白鹭成群结队地飞翔、游弋。这一路走来,我的眼前总是自然诗意的风景图画。
山水的灵秀,催生了西溪流域许多优质的蔬果,最有名的,无疑是枇杷,其中,以上湖枇杷最受人们青睐。
来到上湖村,村书记潘纯友、村长潘继续接待了我们。他们说,有言是“浙南五月碧苍苍,蚕老枇杷黄”,上湖枇杷一般每年四五月份就成熟上市了,比早熟的塘栖枇杷还要提早半个月。这时节是水果的淡季,如桃子、梨子、杨梅、柑橘等都还在生长之中,而色泽金黄、果大肉厚的上湖枇杷已经挂满了枝头。枇杷花开在每年的冬天,每一花束有60到90朵小花,每逢隆冬腊月,百花凋零,枇杷花却冒风雪而绽放,被文人雅士称之为“枇杷晓翠”。到了次年春天,才结出果实,所以有“枇杷秋萌冬花、春实夏熟”和“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等说法。
上湖村共有枇杷园1300多亩,上湖枇杷与众不同之处,除了早熟,还具有个大核小、皮薄色黄、肉质细嫩、香气浓郁等特点。品种10来个,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白沙”“大红袍”是枇杷中的珍品。“白沙”其形略长,外有芝麻斑点,肉软而厚,水份多,入口鲜甜。“大红袍”是“红沙”中的佳品,果皮呈橙红色,果形较大,食之满口生津,产量高,果子又耐于贮运。这几年枇杷产量不断提升,价格有所下降,一般是15元到20元一斤。潘纯友说:我们这里原生态的环境,又加上西溪水质的优越和黄沙土壤,所以出产的枇杷品质优良,这在别处产出的枇杷是难以比拟的。
当地画家潘活泼说:枇杷别名甚多,如芦橘、金丸、芦枝,写它的诗文也多,比如苏轼就有“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的诗句。枇杷是我国传统名果,栽培历史距今已有二千多年,而上湖枇杷的历史相对较晚,约有500来年,明嘉靖时期从福建引进,植株很大,一棵树能长一千多斤的果实。到了清朝,上湖枇杷已名声在外,有商人就在温州城西郭建了枇杷行,有十几间店面。每年枇杷采摘时节,上湖人挑着枇杷,浩浩荡荡,先到桥下韩埠码头,再坐渡轮过瓯江到西郭枇杷行,销往温州地区和青田等地。当时枇杷保鲜用梧桐叶包裹,存放在竹篓里,一个月不会变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办农业,上湖的枇杷树被砍伐,从1983年开始,上湖的群众重新种上了枇杷,是新的品种。
关于上湖枇杷的历史与传说,没有更多的文字记录。历朝历代的果农,他们鲜活的故事、丰富的情节,如秋后蒲公英的花瓣,随风飘去,消失在西溪那滚滚的浪花里。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史书,发现吉光片羽般的旧时影像,比如孙诒让的《永嘉闻见录》,记载有“邑产枇杷,肉薄而核多,惟巡道署及谕署所植,肉厚有独核者,风味不减家乡。”
我们来到了上湖村林垟山的一片枇杷园里,正是枇杷开花的时节,满园的枇杷花洁白如玉、清香扑鼻。潘继续说:世间好吃的果子,果树都是难栽的。但上湖的群众注重管理,苦心经营,枇杷一年比一年丰收。村里也积极联系上级部门,邀请农技专家前来指导,提高大家栽种的积极性。
潘继续有10多亩果园,800多株枇杷。这是一片向阳的山坡,每一株枇杷树都长势良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潘继续好像与这些果树成了朋友,掌握了它们的习惯与脾性,管理起来就得心应手。他欣喜地跟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些枇杷树的树龄都在10年以上,今年一株可以摘80斤以上,一斤以15元计算,就有10万元的收入。可喜的是,上湖枇杷的销路也不用愁,他们没有打广告,但口碑是最好的广告,这几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我抬头遥望,田野上、山麓间,都是成片成片的枇杷林。周遭清静,尘嚣遥远,如洗的心灵与无垠的果园浑然一体。
韩埠老街
昔日繁盛依稀可见
我在永嘉县志办徐逸龙的带领下寻找桥下的文化遗迹。千百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一些遗址上长出了半人高的杂草,在蓝天白云下显得特别沧桑;一些遗址早被夷为平地,建了高楼住宅,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匆忙。
徐逸龙提议我走一走桥下镇的韩埠老街,它离现代社会还有一定距离,上世纪的风韵还一直在那里徘徊。
我们来到韩埠老街已在黄昏,街上少见行人,街两侧的房屋多数为木头结构,两层,一楼用作店铺,不过,早已关门大吉,上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有一间房屋的门开着,门口坐着两位打盹的老人,我们好奇的讨论声干扰了老人的休息,他们问我们哪里人?我们说是来了解韩埠老街情况的,老人们就有了怨言,大声说:这老街拆也拆不掉,建也建不起来,留着有什么用?其中一位老人还用拐杖敲敲门板,门板隐隐颤动,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也在低怨。
谈起老街的历史,老人端凳让我们坐下,又颇为自豪地说:韩埠老街位于西溪下游感潮河段的江边,虽然只有300来米长,但一直商业勃兴,坐贾行商,熙熙攘攘,成为当时桥下的盛景。到了日寇侵犯时,韩埠码头与温州城来往的客轮停开,老街上人心惶惶,行人迅速减少,店铺也变得冷清,抗战胜利后,老街又很快恢复往日的繁华。解放后,老街上发展到40来间店铺,经营布匹、渔咸、食盐、南北货、日用品等,客栈最多,有十多家。最热闹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自乐清、永强等地的渔商用河鳗溜儿载着海货,运来韩埠码头贩卖。韩埠街上每天都有数百人来往,过年过节一般。客栈人满为患,家家户户都是旅馆,连破祠堂里都住满了人。那时候在向客人提供住宿的同时,还要提供饮食,不过,住一天只收几角钱,吃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街上也有饭店,接待嗜饮贪杯之徒,行宴传觞,但更多的是奔劳而多苦的船家与脚夫。
永嘉县志办退休干部李昌贤几次来到韩埠老街,做过细致的调查。据他介绍:韩埠老街曾经是永嘉西部山区通往温州城区最重要的门户。1958年以前,永嘉县政府设在温州城区。那时永嘉境内没有公路,到温州城区只能走水路。水路有两条,一条从沙头到温州安澜亭,渡船费一人两角五分;另一条从韩埠到温州西郭,渡船费一人是一角五分,永嘉西部和仙居、缙云、青田等地的群众都从韩埠过往。李昌贤老家在永嘉大若岩,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温州城里读书,从他老家到韩埠或者沙头,路程差不多,但他都选择韩埠的水路。虽然从老家到韩埠要翻越高高的昆阳岭。
李昌贤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渔民在江上海上敲鮕作业,捕获了大量鱼类,有一些运到韩埠码头销售,上好的黄鱼一斤只卖一角钱,西溪流域每天都有近千名群众挑担来购买。当时我在泰顺中学教书,学校教学也不正常,就回老家了。在家里没有事情做,见村里人都去韩埠挑黄鱼,有一天,我也带上12岁的弟弟来到韩埠老街,下午到达时,当天鱼市已基本结束,剩下不多的黄鱼只卖七八分一斤,比番薯丝还便宜。当晚我们住在老街上的客栈里,第二天天未亮就被街上嘈杂的声音吵醒了。我走出客栈一看,鱼市交易已经开始。吃了早餐,天亮了,我与弟弟来到韩埠码头,买了63斤黄鱼,又大又鲜,每斤一角二元钱。我挑起来就走,开始还算轻松,但到了昆阳岭脚,就挑得很吃力了,到了半山岭,就像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真是寸步难行。这一担黄鱼我挑不到家里,还是弟弟跑回村里叫来亲人救援。
听了李昌贤的故事,我们走到了老街的南尽头,就是韩埠码头,码头上有两棵高大的古榕树,把阳光遮去了大半。码头明显已经弃用多年,留给我们一个落寞的身影,溪岸边留下来的几级石阶,像上了蜡一样光滑,依稀能辨当时商贾云集的景象。今年91岁高龄的姚仁枢老人的家就在渡口边,他与我们一起来到了码头,动情地说:韩埠码头是瓯江北岸永嘉段最大的客货运码头,当时用石头和青石板砌成,客轮昼夜不停地行驶,还有十多只舢板临时调用,而满载货物的河鳗溜儿,每天都把码头围得里里外外好几层。我在码头上做了几十年的牙郎,许多货物就是经过我的秤,从韩埠运出去的。在那个水运昌盛、陆路不通的年代,韩埠码头是一张“金字招牌”。
我问姚仁枢老人:你家正在“金字招牌”旁边,一定坐拥“金山银山”了?老人说:不是这样,我就这么一间房子,家里人口多,住着都拥挤,就没有想到开店了。客商一元的交易额,牙郎收取四五分钱,码头上牙郎几十人,一天下来赚得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公路发展起来,延伸到各乡镇与村庄,水运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到韩埠码头的货船和客人一天比一天少,码头也一天比一天冷清,我们这些做牙郎的,都有些措手不及。九十年代开始,这里的客船和市场都在我们的眼里消失了。老人说到这里,语气中带着几分迷茫和不舍。
大家突然沉默了下来,低头见西溪的水缓缓东流,带着许多不可猜透的谜底和恒久的记忆注入瓯江。但我们在西溪两天的走读中,已经寻找到了鸟的天堂、水的故乡、生命的摇篮,这是大自然的恩泽,也是人们情感的归依和生命的寄托。
本文转自:温州网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跟帖评论服务自律规则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温州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