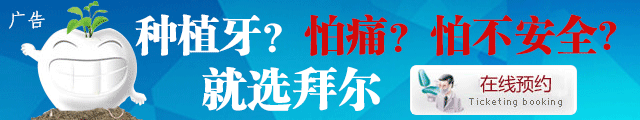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琵琶记》研究的拓荒者
——纪念董每戡先生诞辰110周年

温州网讯 在温籍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董每戡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市学术界将举办纪念活动。董每戡(1907-1980),集戏剧(话剧)与戏曲为一身,兼创作与研究为一体,是近世戏剧理论界不可多得的奇才。历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所著《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被学界称为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尤以《琵琶记》研究著称,被誉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
首撰专著《琵琶记简说》
瑞安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为此发表了大量评论与介绍之作,称其“可师,可法,而不可及”,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同时它又是一本颇有争议的作品,为此,1956年6月,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并上海、广州、杭州、重庆、武汉等地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琵琶记》讨论会。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讨论会先后召开七次,还有一次学术演讲,历史学家翦伯赞作了《琵琶记》历史背景的讲演,戏剧家董每戡作了专题报告。董所用讲稿即是他脱稿于1955年11月的专著《琵琶记简说》,1955年6月由作家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研究《琵琶记》的专著,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部,因为此前除了为该剧写的序、跋、短评及评点外,未见有专著问世。
《琵琶记简说》除了充分肯定《琵琶记》的反封建主题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一是介绍高则诚的身世及其创作《琵琶记》的过程。前者称其得天独厚,“生长在孕育南戏的摇篮地东瓯,半生耳濡目染的结果,爱上了为当时人民所喜爱的戏剧文学,终于自己也成为戏剧作家”,为创作《琵琶记》赢得先机;后者称高则诚出身书香门第,虽早期有浓厚封建意识,但为人正直,为官贤能,爱护人民,及时转变思想,终于写出了像《琵琶记》这样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二是论述《琵琶记》的情节结构。董每戡同意李渔“立主脑”的提法,指出本剧的所有情节均集中在“重婚牛府”一事上,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各种矛盾冲突,揭示主题,可见“重婚牛府”便成了本剧的“主脑”。但他同时又指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最赏识的“对照”法,把蔡家和牛府交错着写出:一边贫穷困苦,一边富贵欢乐,互相对照,从而表现了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哀乐不同,正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令人愤慨的情况。他认为“这样的写法是新鲜的,前人的剧曲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结构,作者在这里确是刻意经营的”。三是细致分析了《琵琶记》的人物创造。着重分析蔡伯喈、赵五娘、张广才三个人物。称蔡伯喈的戏剧故事和王魁、张协两戏文同型,主角的性格容易雷同。由于高则诚是一位有创造性有想象力的人,有意避免雷同,结果,相当杰出地完成了他的独创性,“使他有别于王魁和张协,也不同于后于他的陈世美”,从而“提高了原来民间流传而又被南戏用过的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称高则诚塑造赵五娘的性格时,“把对生活的深刻的洞察力和艺术的概括力雕塑出来,所以真实而有血肉,可说显现在赵五娘身上的民族性,正是由于他的独创性来完成的,而这种独创性在以后的传奇作者的创作才能上,很难找到”。
总之,这是一本全面、深刻而又公允地评论《琵琶记》的著作,难能可贵的是,它的许多基本观点为后人所接受,就专著而言,罕见有人超越它。当年曾经与董每戡同场辩论、意见相左的徐朔方三十年后在《论琵琶记》中检讨说:“我很高兴有机会纠正我自己三十多年前的看法。”
首肯反封建的主题
关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当年的学界,或以为“为统治者宣扬封建道德”,或以为“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针锋相对,因此在1956年北京举办的那场《琵琶记》讨论会上即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凡主张前者的,以徐朔方、陈多、邓绍基等为代表,称为“否定派”;主张后者的以王季思、董每戡以及俞平伯、赵景深、陆侃如等为代表,称为“肯定派”。两派进行近一个月的七场激烈辩论,终使肯定派赢得上风,接近达成《琵琶记》具有反封建主题思想的共识。董先生则是肯定派的中坚人物,他首先在《琵琶记简说》中旗帜鲜明地作了如下的定义:“《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呢?抑是以和人民共通的情感,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呢?从整个剧本所暴露的事实看来,该不是前者,而是属于后者。”继而又在《琵琶记论》中作进一步论断:“谁都知道《琵琶记》以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为主题,但不是除此之外就啥也没有了,至少它同样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的罪恶,这也是该包括在主题思想之内。”意谓《琵琶记》的主题,应包括反封建婚姻制度与科举制度两方面的内容。
董先生为了阐述上述的观点,主要是举高则诚在古本南戏《赵贞女》基础上重新创作《琵琶记》时改“三不孝”为“三不从”为例,进行精辟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是彻头彻尾的“三不孝”,丧尽天良,理应遭到“五雷轰顶”。而高则诚将其改为“三不从”,主题起了质的变化,蔡伯喈的遭遇受到观众的同情,他在“三不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抗行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因此董先生认为作者作这样的安排“直逼到主题思想的最深处”:首先是“辞试不从”,即蔡公逼试,伯喈辞试而不从。这是“整个机器的发动机”,“戏剧境遇中矛盾冲突的起点”,因为后面的“辞婚不从”与“辞官不从”都是从此引发的。这就告诉观众:元代封建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知识分子设置的牢笼,是罪恶之源。其次是“辞婚不从”,这是三个互相依赖的“不从”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矛盾冲突的高潮。蔡伯喈作为有妇之夫,中状元后拒绝再娶,在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可在封建时代,只要宰相之类的高官要你入赘,你就不得不接受,尽管蔡伯喈与此作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也只得被迫接受,招致父母双双饿死,妻子赵五娘罗裙包土筑坟茔的下场。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及其制订者封建统治阶级。第三是“辞官不从”,须知牛丞相是通过皇帝逼婚的,因此蔡伯喈辞婚是“抗旨拒圣”,矛头直指皇上。正如董先生所说:“蔡伯喈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与胆量,公然的真实地提出来,这儿便发出了人民性的闪光,蔡伯喈形象增加了光辉。”这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通过这样的分析,《琵琶记》反封建的主题是谁也无法否认了。
首提“南曲传奇之祖”
《琵琶记》是一本上承宋元南戏、下启明清传奇之作,自明代开始即享有“曲祖”之称,最早出自明魏良辅的《曲律》。由于对“曲祖”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后来又有“南戏之祖”(白云散仙《重订慕容喈琵琶记序》)、“南曲之祖”(姚燮《今乐考证》)、“词曲之祖”(凌迪如《万姓统谱》)、“传奇鼻祖”(陆贻典钞本《元本蔡伯喈琵琶记》题识)、“填词家之祖”(刘廷玑《在园杂志》)等不同称呼,可惜他们都将“南曲”与“传奇”二者分离开来,因此均不甚全面与确切。唯有董先生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南曲传奇之祖”之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正确的提法。他先在《琵琶记简说》结尾说:“因此,我推崇他(高则诚)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大师之一,《琵琶记》为南曲传奇之祖。”后又在《琵琶记论》开头作进一步说明:“《琵琶记》,一向被人们推崇为‘南曲传奇之祖’,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并非因它绝大部分是纯以南曲组成且具有戏剧完整体制的最初一部‘传奇’之故,那仅是形式的新奇;主要是它在思想、艺术上有特别高于时剧的成就;同时,这种成就也不只限于词曲真的如何美好,正因为情节结构的完整紧凑;尤其高则诚创造了我国在此前少见的心理状态那么复杂而鲜明的艺术人物形象,即使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比较也是毫无愧色的。因此,六百年来,这个剧不断的演出,为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所谓‘南曲传奇之祖’的美称,它就无愧地承受下来了。”
董先生的这一提法之所以确切,首先是由于切合戏曲发展的客观实际,因为高则诚所处的时代正是“南戏”向“传奇”过渡之时,而吹响这一时代号角并率先垂范的正是他的《琵琶记》,它既是南戏的巅峰之作,又是“传奇”的开山之祖,兼而有之,故唯有“南曲传奇之祖”才可包容。其次是《琵琶记》体制规格,已与古本南戏有别,而与新兴的“传奇”接近,如剧名(称“记”)、开场、出数、格律以及故事之奇等,均与后来的《浣纱记》等传奇并无二致。正如姚华的《菉猗室曲话》所说:“温州杂剧始于南宋,盛于胡元。元、明之际,正将绝之时,而《琵琶》诸传,变而继之,于斯之时,体格初成,名目未立,不必如后世所谓传奇,姑以戏文称之耳。”意谓《琵琶记》变自南戏,与后世“传奇”接近,之所以不称“传奇”而“姑以戏文称之”,是因为其体制初成之故,一旦成熟了自然即称“传奇”了。可见,也只有《琵琶记》有资格接受“南曲传奇之祖”的美称。第三是《琵琶记》处于“民间南戏”到“文人传奇”的转折点。高则诚是南戏史上第一位文人作家,他重新创作的《琵琶记》不仅是文人传奇的第一种,而且和它的前身《赵贞女》思想倾向正好相反,它继承了民间南戏出类拔萃的艺术成就及进步的思想内容,为文人传奇开了个好头。正如徐朔方在《南戏的艺术特征和它的流行地区》一文所说,在文人传奇的同类作品中,“高明改编《琵琶记》是唯一例外”。可见,也只有《琵琶记》才可称得上是“南曲传奇之祖”。
总之,董先生学识根柢深厚,道前人所未道,颇多“始作俑者”,堪称是《琵琶记》研究的拓荒者与导航者,值其110华诞之际,特撰此文以颂扬与纪念。
来源:温州日报
徐宏图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