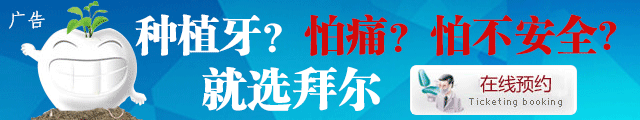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洪禹平文集》代序:这样的一根“芦苇”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帕斯卡尔
一
八月十五日十二点О五分,洪老师——洪禹平先生去世。当时我和几位文友正在快餐店里午餐,汝杰打电话来说洪老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四天前,八月十日晚,他已进人休克状态,照医生的判断,原是那一晚都可能捱不过去的。
今年四月份,洪老师又一次住院。自从五年前大病一场总算转危为安后,他就经常住院,所以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以为和平时一样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来。但这回好像有点不对劲,不管怎样打针吃药,病情就是不见好转。去上海做了一次检查,回来他告诉我,上海的医生说他胰腺里有囊肿,不能动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大碍是没有的。于是他又住到乐清人民医院,继续打针吃药,其间还作了一次肠镜,夹去肠里的几块息肉。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病情不但不见减轻,反而加重了。他自己也怀疑起来,问医生:“我不怕死,你跟我说实话,我的病是不是恶性?你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好做安排。”医生说,有这个可能,但也不能肯定,建议他到温州做一次详细检查。在温州呆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通过熟人的关系,联系到了上海一位治胰腺病的专家,决定再次去上海。这时已是六月下旬了。他第二次在上海期间,我打电话探问他的病情,他说医生还是说良性,只因囊块长在胰腺里,又过大,不能动手术。
七月十一日晚,洪老师从上海回来,这时我们已从他的亲属那里得知,他得的是胰腺癌,且已扩散。只是,上海的医生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
洪老师的身体比原先虚弱多了。从上海回来的那晚上,文兵扶他上三楼,他在家门口蹲在地上好一会起不来。他的两条小腿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一米七六的身材,当年是玉树临风,如今却像是西风中的一根随时都会折断的芦苇。
按帕斯卡尔的说法,人原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何况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且是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候……
可这又是怎样的一根芦苇呵!
二
几天以后,洪老师住进了乐清中医院。在这里,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段日子。乐清中医院的一位名中医到他家看他,给他了几帖中药,服后通便情况大为好转。在西药已经罔有效果的情况下,他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医中药上了。
洪老师原是个非常自信的人,包括对自己的体质。他年轻时练过太极拳和八段锦,在当右派的艰难岁月里,他也不曾放弃过练拳。他经常说,他起码可以活到九十岁以上。不久前在温州文代会上碰见九十高龄的老诗人马骅(莫洛)先生,说起洪老师的死,他叹息道:“禹平啊,他总是对我说他可以活到一百岁的国,怎么这就走了呢。”有人五十不到就说自己老了,洪老师闻而大哂:“什么啊,我五十多岁还在谈恋爱呢!”七十岁的时候,他对别人称他老作家还大不以为然。他对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很关注,几年前一次市文联宴请顾问,他对老画家倪亚云先生说:“亚云,我们只要坚持十年就有办法,那时基因工程就成功了,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到一百岁以上!”我曾开玩笑说,洪老师是秋行春令(年近花甲再婚),冬行夏令(晚年还得为年幼的儿子的将来操心);在他来说,这却是生命力和自信心的体现,为我们这些常人所不及。
但今年四月份他住院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好像已有死的预感。一次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医院,说:“我这次的病有点不样,也许过不了关。我毕竟八十了。我想趁现在神智还清楚,把文稿的事向你做个交代。万一我有个什么,我的文稿就托你整理、保存。我将把这个意思写进我的遗嘱。我这里有都散文集书稿,是我从多年来发表过的作品中选出来的,现在就交给你。还有一部《中国历代书法精品集成赏析》,和一些诗词、小说、散文的稿子放在家里,到时候我也都交给你。就是这部思想自传,还有最后十章没写出,我现在正在修改已写出的三十九章,只要给我一年半载时间,我就能把它写完……”
第二次从上海回来后,他对死的预感就更加强烈了。七月十三日,那时他还没住进中医院,我去他家看他,他让我看了遗嘱的初稿,又捋起汗衫叫我摸他的腹部,说,你看这肿块怎么这样大啊,还是好几块,又是长在胰腺里,要是在别的部位还好些,就是长在脑里也许还可以做手术……他说自己已经不大吃得下东西了,吃下去就吐。他又一次说,看来我这关是难过去了,但半年时间总是有的吧,有半年时间我就可以把自传写完。万一没这个时间,那只好让它残缺了,残缺也有残缺的美,可以让后人去想象。我看他的枕头边摆着自传的初稿,还有一块小木板,是用来搁稿纸的。我心里明白,上帝很可能连这点时间也不会给他了,但又不好说出。我只是建议他还是采取口述的办法,把没写完的几章完成——前天晚上在他家时,我和文兵就这样建议过,当时他也表示同意。
七月十六日上午我又去洪老师家,再次说起口述录音的事,他说已经没有元气说话了,还是等身体稍微好些后自己动笔写吧。他似乎对自己的病又有了点信心,他这点信心是被几帖中药激起的。我知道这时什么药物其实都已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只是企望中医中药能把死神挡一下,让他有时间把他最想做的这件事做完。前一天,我和蓉棣、文兵、锦毅、光灵几位商量过,大家决定抢在洪老师去世之前,把他的散文集《心迹集》印出来,让他高兴一下。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并建议他写一篇自序,他听了很高兴,说马上就写。我又顺势提议,该考虑编文集的事了。我说,你的文集,将来我们总要设法把它出版的。他听了,分明有点激动,说:“若能这样,我一生之愿足矣!”
他的散文随笔集《心迹集》几年前就已编成,并打好字拷在软盘里。(后来我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他五十岁时编定并作了序言的一部旧体诗词集稿也叫《心迹集》,可见他对这个书名多么钟爱。)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文集,真正的学者散文,和眼下充斥报刊和坊间的一些所谓文化散文相比,高下判若云泥。洪老师自己也很看重这部文稿,总想找个像样的出版社出版,但在出版业也被市场经济牵着鼻子走、一切惟利是图的今天,他的这部虽高雅却未必能为出版社赢利的书稿想“嫁出去”并不容易。他没想过自费出版,可能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也和他高傲的心志不相合。但事到如今,也只能走自费出版的路了,出版费用,大家替他想办法。
第二天,洪老师打来电话,说已住进中医,散文集的自序也写好了,要我过去拿。这篇自序写于七月十六日,离他去世只有一个月,是他今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和自序一起交给我的还有一封关文集编排构想的短简,以及《中国历代书法精品集成赏析》的打印稿。这时他的身体虽已极度衰弱,几乎已无法进食,全靠输液维持生命,但还在以最后的一点力量坚持工作。他正在校对他的思想自传已写出部分的打印稿。打印稿用的是五号字,细如蝇头,他躺在床上,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执笔,一个重病人干这样的活,叫我们在旁的人看着都觉得累得慌。我提议让我来校,他说,还是我自己校吧,我可以一边校对一边作些修改,再说,我再看一遍前面的部分,会产生续写后面部分的灵感和激情。我听了,不好再说什么,心里却有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在好些年前,我曾目睹另一位老者,胡牧先生,也是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忍着剧痛,整理他的一部地方史研究著作《瓯史初探集》,直到完工以后才去住院,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这本著作的出版。胡牧先生去世后,我写了一篇《胡牧先生》,发在《浙江政协报》上,后来又收进我的散文集《听蛙楼琐语》里,洪老师在为我这本散文集写的序言中提到它,说是一篇好作品。其实作品不见得写得好,是这两位前辈精神上有共鸣。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说的三不朽,在欲立功而不得的情况下,就守住立德立言,锲而不舍,令人感慨感叹。而其中尤以身处“边缘”的那些前辈学人,名虽不彰而之死靡他,冷板凳一坐百年身,真叫人不知何以为情,情何以堪!这样的前辈,现在是去一个少一个了。
洪老师曾经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然而正当盛年而忽道变故,从“中心”坠入“边缘”,命运一落千丈,繁华顿歇,二十多年间的日子,就像他最喜欢的杜甫诗里说的那样“到处潜酸辛”,“改正”之后虽余霞尚赤,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返归“中心”,以“边缘”之身终老牅下。而心气却是愈老弥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志”不是范仲淹说的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一种更为深广的人世关怀。
握着笔杆子倒下的文人,和战死沙场的将军,一样悲壮。
三
洪老师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最近我看到一张卫生小报上一篇文章称胰腺癌为“癌中之王”,死亡率极高,几无生理,而且一旦被确诊,离大去之日就不远了,而我原先总以为他还有一点时间,半年,几个月,以为他还能看到已经交到出版社的散文集的出版,更能看到已在印刷中的《乐清书画集》——这本书画集收有他的一件书法作品,他在住院时几次问起书画集何时能印出。
入院不久,他就开始感到疼痛了。虽还没到剧痛的地步,却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痛感,哪怕不很剧烈,也够折磨人的,何况是对一位单靠输液维持生命、体力已消耗殆尽的老者,何况这种痛感还日甚一日地在加剧。我常去医院看他,每每见他难受得把头深埋下去,试图减轻难受的感觉,有时也忍不住发出声音。雇来护理他的男护工告诉我说,他难受的时候老是叫妈啊妈啊。洪老师听见了,就反驳说(这时就又显出了他好辩的性格):“不叫妈啊叫什么!”转而又对我和他的胞姐洪禹华女士说:“也不知什么道理,八十岁了还总老是想着妈。以前也是这样,生病时一梦到妈来了,病痛就减轻了许多。想起来,我们兄弟姐妹中,妈也是对我最好了……”末尾这句话,就是只对他胞姐洪女士说的了。接着他就和胞姐聊起小时候的事,好像连病痛也暂时忘却了。
他的思想自传只校对了五章,已无力继续校对下去了。他对我说:“我做不动了,只好请你替我校对,真麻烦你了。”
我在校对完北京特快寄来的《心迹集》后,就着手校对他的思想自传。本来,洪老师的字写得极好,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写得又认真,看着都是一种享受,也易辨认,但这部思想自传稿本却不一样,那是来不及誊录的草稿,大部分部分章节笔迹相当潦草,而且许多地方都做了修改,修改时增补的文字字体小而笔迹更潦草,因此读稿本就常常需要“破译”。这二十来万文字,实际写作时间不到半年,是他在写作激情燃烧中写出来的。那段时间他很少外出,偶时打个电话过来聊几句——都是他写到得意抑制不住奋的时候,说:我的状态好极了,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是在这部书的写作中燃尽的,读着这书,让人不由得想起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是一部大爱之书,爱亲人,爱备受苦难的民族,爱历尽坎坷的祖国,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又是一部大恨之书,恨一切形形色色的专制,恨人间的不平、不公,恨一切践踏文明、扼杀民族生机的倒行逆施。
深广的忧愤,深刻的反思,出之以充分的学理,载之以精彩的文辞,没有他这样的经历,胆和识,学力和学问,以及文字上的功夫,是写不出的。
最初认识洪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文化馆召开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其时他五十多岁。记得那天他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是那时候很时尚的服饰,显得风度翩翩而威严——那是一种学者、绅士和“老革命”几种身份糅合于一体的风度和威严,仿佛二十多年的磨难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痕迹。他的在场似乎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的发言显得有点张皇失措。他也看出了这一点,就鼓励我说,你大胆说吧。后来我和他交往渐多,对他了解渐深,发现他象是个十分亲切的人,可以在他面前放肆,而他的博学,他的雄辩,他的激情,他的坚强,甚至他的天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有没有脆弱的时候?他有没有落泪的时候?我不知道。
但在他病重的时候,在校读他的思想自传的时候,我看到了,看到了他流泪的场面。
一次,他谈到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他的历史随笔,他的经典述要,他构思了半世纪、也曾写出第一部几十万字(毁于“文革”时)的、总体计划达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路漫漫》(最初叫《命运》),都不可能完成了,甚至他的思想自传,都可能成为残缺之作,这时我发现他的眼角洇出了几滴清泪。另一次,我和锦毅夫妇去看他,锦毅拨通了远在外地的老同学、也是洪老师的学生谢中旭的手机,让洪老师和他说话,这时我又见洪老师流泪了,他哭着说:“中旭啊,你还不来看我?我想你啊……”在他的思想自传里,我看到有一处文字描述自己的哭,那是在“文革”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善良的前妻迫于形势提出和他离婚,离婚是通过乐清法院来处理的,“法院的人带着我的签字走了以后,萍儿(引者注:洪禹平先生的一位远亲)正好来看我,见我坐在床前的方桌边发呆,泪流满面,她便在我身旁坐下,双手捧着我的手说:‘阿公,为什么这样难过?……说吧,说出来会好过些……’”
在他去世后别人的纪念文章中,我也看到一处他流泪的文字,说也是一位老人,他在老年大学的学员,去医院探望他,他泪流满面地向她背诵了弘一法师临终时的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一个情字,便是他的思想自传和一切著述的立足点。在这里,情不仅指男女之间的爱情,亲朋之间的亲情友情,那是广大得多的一个范畴,上接天地,遍及人间。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会为一般人所不愿为不敢为之事。比如,当年他在温州一位朋友口里得知林昭的事,竟以戴“罪”之身,于食不果腹的艰难之际,筹措路费,跑到连居委会老太太都虎视眈眈的上海,试图找到素昧平生其时正危如卵石的那位北大才女,想说服她不要徒招牺牲。
四
我可能已经太多地描述了洪老师的“流泪”。其实,哪怕是在重病之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他的天真。
我曾经以《诗人天真》为题写过一篇短文,写一位我素来敬重的九叶派老诗人,以为这老诗人能把艺术青春保持到老,凭的就是天真。我所谓的天真,就是赤子之心。没想到这篇短文在报上刊出后,惹得那老诗人很不高兴。据说他是听一位亲友说的,说我在报上把他生活中那些可笑的事都抖露出来了。我不知老诗人自己有没看过我的拙作,反正他的意见挺大,告诉我也熟悉的几位朋友,说乐清的许宗斌怎么对我有意见啊。这事真叫我哭笑不得,很想找他解释一下,又觉得解释是多余的。老诗人今年年初也归了道山,想解释也无从解释了。
我在那篇短文中写过一件事,就是那年我和洪老师、老诗人三人结伴绕道上海到杭州参加省文代会。在轮船上,洪老师和我拉老诗人一起去餐厅吃饭,老诗人死活不去,只在房间里啃他带去的冷馒头(他带了一袋子),因为他怕窃贼偷了他的诗稿。到上海后,他嫌宾馆的宿费贵,掉头就走,说带我们去个又好又便宜的去处,转弯抹角半天,结果把我们带到一家开在地底下的末等旅馆里,宿费果然便宜,一人一天六块,可夜里连解手的痰盂还是开口向他们要后才给了一只。老诗人却宾至如归,睡得十分香甜。洪老师笑着对我说,老唐啊,在温州街上拉了多年板车,苦惯了,让他在这里住一个月都能安之若素。
我把老诗人对我有意见的事告诉了洪老师,他说,不必放在心上,这其实也是老唐的天真:轻信人言。
其实,洪老师也是天真之人。只不过,他的天真和老诗人的天真不一样。洪老师的天真,表现为一种常常和世情杆格的持续到死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常常被人误解为“说大话”,误解为不切实际。比如,他以垂老之身热心筹划办雁荡人文学院,办《山水文学》、办《学术小品报》。又比如,他对基因工程的那种热切企望,他还是足球迷——很可能是中国最年老的足球迷,每逢国际大赛,他比年轻的球迷还兴奋,浑身血脉贲张,碰上这样的时候,他到文联来就大侃足球,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十几年前,那时他的儿子轲轲还只是几岁的小孩,大概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又一次败北,他愤怒极了,就说,我准备让轲轲去踢足球,将来当球星,“一脚踢过去就把对方踢死了!”说到这里,他极为解恨地笑起来。这次住院期间,正逢中韩之战,当他听他胞姐说起我方门将扑住韩国球星李京国主罚的点球时,他“情不自禁地举起骨瘦如柴的双手击掌相庆”。
洪老师最让人揪心的一次“天真”,发生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已经被疼痛折磨了好些天,开始怀疑医生的话了。有一次他对我说,与其这样难受,还不干脆死了的好,一了百了。对生死,他早就想过了。“我爱生,留恋生,可也不‘怕’死……”他引庄子的名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表达对于死的坦然。他怕痛而不怕死,因为痛会
使人失去尊严,而死不一定会。选择死而拒绝痛,这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隔几天我再去看望他,想请他辨认一下自传手稿上一些我无法“破译”的字句,正逢他服了药,沉沉欲睡,我只好退出。到了傍晚,忽接他的电话,声音异乎寻常的响亮,可谓精神百倍,他兴奋地说:“今天早上我吃了仙丹,现在一点都不痛了!没想到,这药还是一位普通医生开的,效果却这么好,世上的事情真是难说啊。现在医药也的确发展快。真是仙丹啊!”我一听,心里就有数,医生开始给他吃止痛药了。晚上我跑到医院,他重复了电话里说过的话,又补充说:“看这样子,我的病也许就能好起来,过两天看看,如果稳定下来,不再痛了,我就开始工作。”又说:“医生要我每隔八小时吃一粒,不痛时不吃,我想是不是可以吃两粒,那样也许好得更快些……”唉,他这么一个冰雪聪明人,怎么就意识不到医生给他的是止痛药,而非什么仙丹,这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才能判断啊。当然,可以解释为求生的本能使他轻信了医生“善意的谎言”,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他的“天真”使然。天真的人总是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他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我已经对你表白过了,我不怕死,你该告诉我的病的真实情况,我好安排我的事啊,他以为这样说了,人家告诉他的就是真实情况了。
就在他开始吃“仙丹”后的几天,他的病情急遽恶化,进入了休克状态。早已摆在病房里的氧气管开始工作。监护器上显示的血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
五天后,洪老师去世。
五
洪老师已以他自己生前选定的方式安眠在故乡的山野上。那里有松树,还有杜鹃花。他曾有诗道:
自谓平生不爱花,偏为杜鹃喜欲狂!
一随无边原上草,丹心碧血引春光。
(《杜鹃咏》)
今年三赋杜鹃花,一赋杜鹃一迴肠。
不似少陵收彩笔,海棠虽好不留芳。
(《又一首》)
三赋杜鹃的另一赋,是指《寄王君》(王君,王思雨先生,画家,作者好友),此诗中有句道:“最喜龙湫天上落,飞涛影里杜鹃红。”他还有一首七绝《狱中春》也写到杜鹃花:“花事如何君莫问,绿林自有映山红。”
他喜欢的花是杜鹃,喜欢的诗人是杜甫。杜鹃花有栽培的也有野生的,他喜欢的是后者,春天里中漫山遍野如火如荼的那种野杜鹃,又叫映山红。杜甫,晚年自称“少陵野老”,也有一个“野”字,其时杜甫早己不当左拾遗的小官,漂泊西南天地间,十足的边缘化了(就是在诗坛上,当时的杜甫也不是处于中心位置),人诗俱老。杜鹃和杜诗,因此很契合洪老师的心境和性格,无怪乎他在诗文中屡屡提及杜鹃和杜甫。
在当“右派”的艰难岁月里,身处江湖之远,于辛苦恣睢谋生之余,他曾立志“将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断代史、文学史、杜甫这样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的专题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一部《杜甫评传》,“借此知人论世,表达我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一些最重要的看法。”(引语见《百年悲笑)第十六章)他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科,并写了许多札记,为《杜甫评传》的写作做准备。可惜这些资料和札记全部毁于“文革”之中。“文革”后,他转而研究谢灵运。这又是一位从“中心”坠入“边缘”的大诗人,而最终死于虐杀的结局则比杜甫死于贫病更为悲惨,因在温州当过太守,屐印留于我们故乡的土地,大量光芒万丈的山水诗杰构产生于斯,加上谢灵运头上笼罩着种种历史迷雾,使他产生了研究的浓厚兴趣。研究的初步成果见于他的《千古诗魂——谢灵运研究文集》。
熟悉洪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但我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尤其是在读了他的思想自传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他的学问之博之深。现在文坛上也有一些作家号称学者型,比如王蒙、刘心武等,因为会谈谈《红楼梦》,别人遂以学者型视之,其实论学问是不能和洪老师相比的,尽管他们现在的知名度比洪老师高。关于洪老师的学问,有他的著作在,不必我来饶舌。我想告诉别人的是,他读得书多。“他读得书多”这话本是钟叔河先生说周作人的,那时钟先生冒着点不韪整理出版周作人的书,他在《〈知堂书话〉序》里说的这话,多少带点找理由的味道。不能说洪老师读书之多堪和知堂比肩,但以我的眼光看来他的读书之多已少有人可及了。从二十四史到《资本论》,他都通读过了。还有我碰都不敢碰的康德他也很有兴味地读了,谈起康德如数家珍。康德是他最为服膺的一位西方哲学家,他对康德的不可知论尤其佩服。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经典作品读得更熟,人家这是少年功夫,少壮不努力如我者现在再怎样努力也是无法企及了。
读书多不等于就有学问,读而不思充其量只能读成个两脚书橱,不及电脑万一。洪老师的读书,是思考型的读书。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他问我,周代商,都说是一场推翻暴政的革命,司马迁何以要歌颂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曾想过,没想通,最后还是信了毛泽东的说法:司马迁歌颂错了。洪老师说,是的,以前我也认为司马迁歌颂错了,最近又读了一遍《伯夷列传》,有了新的理解,我觉得司马迁是主张反对以暴易暴,伯夷、叔齐反对的就是以暴易暴,所以太史公歌颂他们,这是非常超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听他这一说,真有醍醐灌顶之感。
我说洪老师是学者型、思想型的作家,因为他除了有学者的专(比如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也有杂家的博,更有思想者(我不说他是思想家,是因为我对思想家的定义还弄不清楚)的深刻。本来,他要在他的思想自传的最后几章集中谈他的一些思考已久的学术观点,可惜书未成而斯人遽尔而逝,“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惟平时闲谈之间,尚记其片言只语,如吉光片羽闪烁于眼前。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那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每根“芦苇”,之间还是有大差别存焉。有的“芦苇”也在思想,但想的只是玉堂金马,妇人醇酒,天地良心与我何关,宇宙苍蝇管他的娘,这样的“芦苇”虽生犹死。
洪老师死了,但也这根“芦苇”——帕斯卡尔所说的高贵的“芦苇”,真正能思想的“芦苇”,他会活着,他留下的文字就是他活着的依据。就像他的骨灰撒落的那片山野,八月的杜鹃没有花枝,但根子却在,明年春天来临时就会再度开出火红的花朵。
2005.9.3完稿,乐清听蛙楼
作者:许宗斌
水云绵远——许宗斌纪念文集
《水云绵远——许宗斌纪念文集》是一本纪念许宗斌老师的纪念散文集。许宗斌(1947—2015),浙江乐清人,生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乐清市文联主席、乐清市社科联顾问、乐清文献丛书主编、《雁荡山志》主编,著作等身,学识丰厚,一些著作成果、研究方法、写作模式,尤其是《雁荡山笔记》具有全国性影响,被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多次称引,被认为是温州地区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比较突出的作家和学者。许宗斌去世后,本地领导、生前友好、同事、亲属和学生辈撰文予以纪念,并于逝世周年之际召开座谈会回顾其生平与成就。以上纪念文章及座谈会发言,既概括许宗斌一生履历和成绩,又具有特定年代、典型人物的史料价值。为此,乐清市社科联、乐清市文联决定联合编辑、出版这部纪念文集,一以资怀念,又可为后学提供模范。
《洪禹平文集》辑录洪禹平先生生前已发表、出版的绝大部分作品与部分已整理手稿。上卷为中篇小说和散文,中卷为学术论著(主要是中国历代书法精品集成赏析),下卷为学术论著(主要是对书法、诗文经典的评论)和诗词、联、书信。本书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