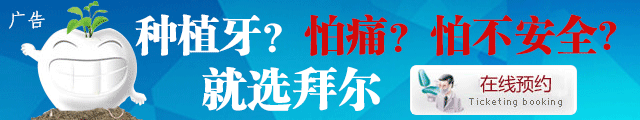渠川忆温州文友

唐湜(右)与金江(中)、马骅在一起。

唐湜与渠川(右)在一起。 资料图片
老作家渠川先生以长篇小说《金魔》著称,他的人生叙述也像长篇小说,一章接着一章,如潮水般浩荡。在他的脑海里,保存着何琼玮、马骅(莫洛)、唐湜等温州文化名家的许多记忆,虽然他们仨都已离世多年,但种种往事,依然鲜活。而我,仿佛是一个深陷故事的读者,读来津津有味。
忆何琼玮:
为人处世多了江湖义气
一纸调令让渠川实现了从工厂到文化部门工作的愿望,那年是1980年,他51岁。渠川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日子,惠风和畅,他到温州市文化局报到,局长方家溪,也是刚刚走马上任。那时百废待兴,全国的文艺工作从“十亿中国人,八个样板戏”起步,温州市文化局正在抓文学创作,举办征文活动,来稿很多,渠川与早来局里一年的何琼玮一起看稿评稿。
何琼玮瘦长的身子,干净清亮,比渠川大一岁,是位剧作家,1957年他创作的瓯剧《高机与吴三春》,演出后大获成功,可让他红火的却是短篇小说《接到讣告以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又被《小说选刊》选载,成为温州市第一位上《小说月报》的作者。不久,文化局成立创作室,渠川为主任,何琼玮为副主任。第二年,文化局又酝酿要创刊一个文学刊物,在何琼玮的提议下起名《文学青年》,他又出点子让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当时茅盾先生已卧病在床,但欣然答应,这也是茅盾先生最后一次题字。《文学青年》很快办起来了,渠川为主编,何琼玮虽为副主编,却承担编刊的主要工作。
渠川先生回忆,何琼玮写稿编稿充满激情,他当时在写《吴百亨传记》,却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编辑刊物上。1982年5月,温州市文联成立,《文学青年》划归文联主管,虽然渠川与何琼玮都到文联工作,但两人都不再做编辑工作,渠川为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何琼玮为文联副秘书长。渠川还兼文联机关支部书记,第一次开支部委员会,他就提议吸收何琼玮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温州市文联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便是何琼玮。
何琼玮早在1945年1月就填写了入党表格,交给了组织。那年他17岁,参加了地下党的交通工作,为游击队购买药物及电池等,又经过严密策划从亲戚家取来崭新德造木壳枪和多发子弹,投奔永乐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父亲何邦英起初依靠祖上留下二十亩土地的出租,开办酿酒作坊,越做越大,又开办了酱坊、孵坊和糖厂等,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利润可观,逐年购进农民土地和破落地主大批土地,达六百亩之多。在抗日战争期间,何邦英帮助游击队抗日,甚至卖掉两百亩土地支持抗日,那时何琼玮还只有十来岁。
渠川先生说:“有人觉得何琼玮像个商人,这是因为长期下放劳动,为了生存,后来有机会做了一名供销员,这难免要动嘴皮子推销产品。在俗世里,没有一股‘适者生存’的生命力,怎么能活下来呢?这要客观。也许正因为做了供销员,他社会关系多,为人处世多了一分江湖义气。1983年浙江省作协在临安举办笔会,让我和老何去一个。他问我:你想去吗?我说:想去,笔会有半年时间,我可以在那里写个中篇。老何就答应让我去。我发表在《海峡》1985年6月号的中篇小说《皇帝陵墓和战俘的坟》,就是那次笔会期间写的。他有什么好事,不忘与他相同命运的朋友,比如他对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剧作家尤文贵就很关照,带尤文贵去福建做生意。后来尤文贵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重新创作,把内心的想法倾泻在稿纸上,出了不少好作品,而老何的创作热情渐退,那时没有一心一意搞剧作,也没有出好作品,有些可惜。”
忆马骅:
冤屈终于平反
《文学青年》创刊不久,编辑们便感觉到刊物的大批业余作者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作品质量不高,市文化局负责同志要求渠川牵头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渠川欣然领命。文学创作学习班很快办了起来,租用温州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室,聘请了讲课老师,招收学员一百多名。在温州教师进修学院教中国现代文学与写作的马骅,也应邀给学员讲散文创作。渠川与马骅的情谊,就这么开始了。
渠川说:“马骅那时66岁,比我大13岁,我们一见如故,我一直视他为前辈。他已从杭州大学离休多年,被温州教师进修学院聘请,在教书之余编写教材《写作基础知识讲话》,大家都尊敬地叫他‘马教授’。他气质儒雅,为人谦和,温厚中带着刚毅,对待学员有一种慈爱,教课时语言活泼,他上课时我去听,他说‘散文形散神不散’,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点。”他听说“马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末被作为“叛徒”受到冲击,深觉不可思议。
1980年,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到1984年年底平反工作即将结束。渠川心想,马骅怎么都没要求呢?他就主动去找马骅,说:你的事自己估量估量,是否要申诉?马骅认真地盯着渠川,底气十足地说:“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渠川说:“那好,我愿意为你跑一跑。”当时温州许多人认为给马骅翻案不可能,渠川却很有信心,在时任市委书记刘锡荣的关心下,渠川开始外出调查。
1985年春夏之交,渠川带人去了上海,再辗转北京、杭州等地,坐火车赶汽车,日夜兼程,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调查,事情终于明了——马骅自1941年从苏北根据地回温州后,温州地下党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已由城市转入农村、山区,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42年,马骅生活在温州,过着紧张不安的日子。1943年1月,将要过年时,由于叛徒出卖,一个深夜,他在温州家里被捕,在牢狱里关了半年后被释放。出狱后他与党的关系没有接上,但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曾任温州地委副书记兼温州市委书记的胡景瑊就证实,1945年在他担任中共瓯北中心县委书记兼永乐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时,有什么困难,常派交通员来找马骅帮助解决。许多证人都是高级干部,证实自己在地下党工作时受到马骅的接济。渠川每走访一人,最后都要问一句:你看马骅同志是清白的吗?回答都是“清白”。
外调结束已是7月,骄阳似火,渠川回温州后马上向组织和宣传部门汇报,组织部又向刘锡荣书记汇报。能否给马骅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却一时定不下来。直到那年腊月二十三,渠川受温州市委组织部委派,带着马骅的外调材料和个人档案,到浙江省委组织部要求审查定性,经过一天的审查,结论是:马骅不是叛徒,恢复党籍。渠川一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悬在心头的大块石头终于落地。腊月二十四,车站人潮拥挤,车票难买,渠川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开往温州却已坐满乘客的小面包车,蹲坐在司机身后过道里的小板凳上。小面包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开得飞快,乘客被车辆急转时的惯性甩得东倒西歪,惊叫不断。车到温州已是深夜,温州城风厉雪飞,渠川却没有感到寒冷,心中似有一轮暖阳。
忆唐湜:
他像飞过长空的大雁
渠川与唐湜的认识,也缘于《文学青年》创作学习班,渠川知道唐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高,就请他来给学员讲诗歌创作。当时唐湜刚刚复出文坛,可以参加文代会,可以创作诗歌,但因长期遭受迫害,做事小心谨慎,写作心有余悸。当时的温州,像唐湜这样在浙江大学外文系正统学习过西方文学的几乎没有。
渠川一直对唐湜十分钦佩且心怀敬意,他说:“唐湜敦厚、善良,书生气极浓,一眼就能看出是位没有一点坏心眼的人,令人疑惑的是,这样一位绝对的好人,温州文艺界有些人对他不够尊重,我觉得不应该。他口才不好,嘴有点拙,上课时课堂效果也不好。”
唐湜比渠川大9岁,因此,渠川1947年考进燕京大学读书时,唐湜已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进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开始了叙事长诗和十四行的探索,并尝试着用一种诗意的散文来抒写评论。学生时代的渠川酷爱文学,也阅读何其芳等诗人的作品,却没有听过九叶派的诗人,尽管那些诗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站到了当时中国诗歌的前沿,写作规模和成熟度都呈加速度态势,有了杰出的成就。渠川说:九叶诗人的名气当时不怎么响亮,没有在文学界走红,是因为他们热衷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沉醉在朦胧的色彩、古典的意象和罗曼蒂克的梦幻中,把欧洲诗人喜欢的十四行等引到中国,太洋气太冷门,曲高和寡,懂的人很少,欣赏的人很少。当然,“九叶派”的提法是30多年后的事情。“我们当时崇拜的大多是抗战诗人,比如田间和艾青,田间在艺术上追求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艾青的诗作富有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渠川说:“我知道唐湜经历了二十年的人生悲剧。1961年他回到温州,连永嘉昆剧团的临时工都不能做,只能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劳动,干拉板车等体力活。他板车拉累了,坐在路边休息,屁股下面垫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见,九叶诗人受莎士比亚以及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派作品的影响有多深。”
唐湜的生命,在苦难的浸润中结出特别丰饶的花果。他内心里的悲哀、凄惶与煎熬,通过创作得到解脱,笔端之下是芳草萋萋,溪水潺潺。渠川无限感叹:唐湜那些曲折回荡、富于感性又通于思辨的诗作,无疑比直接诉苦的诗句连缀更让人喜爱,像他的《幻美之旅》,把眼泪蘸于笔墨,绽放出不朽的优美动人的诗歌花朵。这真是一个高明的诗人,他像飞过长空的大雁,虽然带着苍凉和悲伤,却一往无前。
马骅恢复了党籍之后,唐湜有一次来到渠川家里,他“右派”的帽子已在1979年摘掉,是想让渠川帮助他恢复党籍,这时渠川才知道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加入共产党。渠川当时的心思全在创作《金魔》上,没有时间帮助唐湜,为此一直心存内疚。2005年1月唐湜去世,渠川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唐湜遗像两旁的主联是诗人屠岸的挽联:“沉冤廿载,硬骨铮铮不屈;斯人远去,诗卷煌煌不朽”。是啊,今生就此别过,确有许多思念和不舍,但作品是作家生命延续的载体,唐湜的诗歌还在,那些美好的记忆就不会消失。
来源:温州日报
曹凌云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