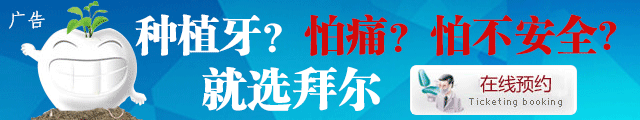梦绕栏杆桥——我的童年旧事

栏杆桥村河水涟漪,古榕婆娑,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尤家宅院坐北朝南,门墙开阔,倒影平河,是幅很优美的图景。 本文图片由孙崇涛先生提供

尤家宅院的老门台。
我的学生叶国林在微信圈上发了一组照片,照片总题:“栏杆桥水乡田园”。
栏杆桥,呵,好熟悉的地名!它藏在我心底已近80年,时时会成为我睡梦的片段和记忆的颗粒,把我带到那遥远的“国破山河在”的岁月……
“逃反”岁月
抗战时期,温州地区于1941、1942、1944年间,三次沦陷。第一次,1941年4月19日,日兵从我家乡瑞安飞云江畔东山村登陆,在占据瑞安城后,北上攻陷温州市区。史称“四一九事变”。
日兵的这次进犯,来势凶猛,上有飞机狂轰滥炸,下有大炮、机枪开路,行动迅速,瑞城民众猝不及防,纷纷从北门倾城出逃,慌不择路,不少人都跑到山上躲避。
那时我还很小,不满三岁,只有丁点的朦胧记忆。父母还年轻,母亲25岁,父亲27岁,带着能跑几步路的我,往北门外山上野草、荒路、岩石间东躲西藏,边跑边躲避头顶上盘旋的日机轰炸、扫射。我记得母亲一直牵着我跑,身上没带什么东西,父亲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后来想来,那准是盛放家中金银首饰和钞票一类贵重物品,为备日后“断供”时费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多记忆了。也不知道这回出逃落脚何处,后来又怎么回到城里的。
还有就是时时听父母说起的,小我一岁半的长妹和她的奶妈,由于逃得仓皇,来不及跟上家人,离散了。好心的奶妈便把妹妹抱到她自己乡下家中躲避去了,直到日本兵退去好久,才返回城里家中。
日本兵退后的瑞安城满目疮痍。大沙堤、小沙堤、殿巷一带,到处是被日本飞机掷下的燃烧弹炸毁的民房,满地砖头烂瓦,多年不见修复。这是日军侵华留给家乡人长久的罪恶、耻辱的图景记忆。
一位男子一辈子被人叫做“炸弹娒”。日本飞机炸弹炸死了他全家人,只剩下他一人因为出外玩耍逃过一劫。他顷刻之间成了没爹没娘没亲人的孤苦伶仃的小孩,大家不知他叫啥名,就一直叫他“炸弹娒”。
家乡人爱把抗战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的日子唤作“逃反时期”。这是没文化人的不正确的叫法:日本进犯中国,是彻头彻尾的外敌侵略,不是内乱,何“反”之有?
次年,外头风声依然很紧,时时传来日兵又要进城的消息,家里决定提早“逃反”。作为瑞安城著名商家、最大绸布商铺的“孙大昌”,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套着好些小家,掌家的叔公家,本人父母长房家,叔父二房家,长年寄居本家的舅公家等。遣散了所有雇员,尚有大小20多家口需要维持,货物也需要转移。于是就于1942年开春,在飞云江南岸“林垟”的临水街面上开设了一间“分店”;“小家”也赁屋分居在林垟各处。由于时局不安,经营惨淡,很难维持生计。不久,掌家的叔公就决定撤销分店,让“小家”各自寻地“逃反”。
同年初夏,我就随着父母迁居到栏杆桥村了,算是躲过了不久日兵第二次进城,即史称的“七一三事变”。
“吴兴旧家”
位于瑞安、平阳两县交界处的栏杆桥村,如今属于平阳县万全镇宋桥社区。此地村以桥名,可见栏杆桥地位不比寻常之桥。流经全村的直垟河(俗称“门前河”),横跨河面的青石桥,百年森森的大榕树,和我家赁居的那座尤家大宅院,是栏杆桥村最夺人眼球的四大景观。
尤家宅院坐北朝南,门墙开阔,倒影平河,是幅很优美的图景,它巍巍乎占据村的中心。据称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屋后还有1300平方米的花园,合计2000平方米。正屋门面五间,二进,带东西厢房六间。我家被安排住在东厢房的一间。房舍格局、模样,至今仍如旧,不曾有过变动。近来有老平阳中学的学生陈玉茹专程去那儿帮我拍摄了我家曾经居住的房间门面和房间内部的照片。我见之不禁心跳,这不正是我当年天天跳跳的熟悉场所吗?
记得我家刚搬进那天,我因新鲜感而兴奋,见地面空旷,不等家中带来的那张钢管床装搭好,就先在地上做起了戏曲里的“起霸”动作。那些年,家里人已带我进剧场、去庙会看过好些戏曲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戏里武将出征前的一套漂亮动作,后来知道那叫“起霸”。虚龄五岁的小男孩嘛,只知图快乐,爱折腾,哪还晓得眼前正是国难当头,身处流离失所的境况。
宅院里住着好多户人家,也不知哪是主人,哪是住客。过了一些天后,才见一个自名“阿田”的比我稍大的男孩主动跑来找我玩,他长得虎头虎脑,盛夏季节,光着脚丫和上身,只穿一条短裤。而我,却是上身短袖衬衫,下身吊带西装短裤,脚套凉鞋,梳个“飞机头”,像个当年电影里的“洋场恶少”,感到“城乡差别”实在是大,不禁对阿田的自由随便羡慕起来。
现如今所见宅门的题额和门联,估计是2013年修缮时加的,那时还不见。门庭额题“吴兴旧家”。门联写作“东瀛学子情系桑梓,书香世家声蜇乡裡”。下联显然有误,“乡裡”应作“乡里”;“声蜇”不知所云,即使想表达宅门主人名声响彻乡里,也应当写作“声徹”为是。不过这副门联倒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宅门主人的基本面貌。情况就如门口那块圆石刻石中所道:
“旧宅主人尤升兰(1872-1939),名于岸,字升兰,亦称声兰,清光绪间廪生,曾东渡日本留学,于宣统元年(1909)毕业于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归国后,拥护民主共和,积极参加平阳光复活动,并致力家乡教育事业,为平阳近代教育先行者。1913年至1917年间,担任平阳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因办学成绩显著,获民国政府颁发的嘉禾奖。同时,尤升兰对乡里人很是帮扶,尤其热衷公益,屋前的青石栏杆桥就是他发起重建的。”
可见宅子主人非寻常人物,无论经历、地位、声望等,在当地都首屈一指。他在我家入住前三年已去世。旧宅既然是在他手中始建,当然不可能如刻石所说“始建于明末清初”,若说是“始建于清末民初”,倒较近乎实际。
旧宅主人尤升兰已是地道的平阳人了,“吴兴旧家”的题额出处,来源于姓氏郡望之说。“郡”为行政区划,“望”谓名门望族,“郡望”即谓某地为众人仰望的贵显家族。或许尤家的先祖来自浙江吴兴,认祖归宗,就以自己郡望地称为“吴兴旧家”,它并不意味旧宅主人或长辈是生于吴兴。
栏杆桥边
栏杆桥,是栏杆桥村的标志,是代号;它栉风沐雨、迎寒历暑近五百年,承载了这方江南水乡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历史全部。有关桥的历史兴替,已引起平阳文管部门关注,研究人员审读地方史志、文献,实地考察、查证,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栏杆桥应始建于明嘉靖癸未年(1523),1920年因台风刮倒一侧榕树压塌桥身,以致损毁,1923年由尤于岸、伍文募集重建。”(平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彭海萍《平阳栏杆桥历史状况初考》)我想这应该是对的。栏杆桥建桥历史之早,居栏杆桥村众桥之首;民国平阳县志误将它认定为“万历桥”,实际是本村的另一处古桥。
栏杆桥斜对“吴兴旧家”大门,二者相距不过十来步。古桥、老宅相倚成趣,加之跟前河水涟漪,古榕婆娑,河岸平坦,石凳罗列,是村民、路人歇脚休闲,谈论古今,闲扯家长里短的好去处。
笑不露齿、足不出户的母亲,脚步的最远终点是老宅大门,而且多半是为了买鱼才带我到那里倚门而立。母子俩也趁此顺便打量一番栏杆桥头的人生气息。
母亲向河里渔夫买鱼的过程,可称是最古朴、最原始、“最水乡”的一种交易方式。一听到外头隐约传来笃笃的竹梆声和“卖鱼呵”的吆喝声,母亲便放下手中一切,端起一只洗菜盆子,牵着我快步走到门口等候。这时,只见一只小巧玲珑的蚱蜢船箭似的从直垟河面上闪射过来,朝着母亲“买鱼哎”的招呼声,迅即停靠在宅门前的河坎边。船尾坐着渔夫,手持单桨,头戴斗笠,下雨天还会穿身蓑衣。船内盛放鱼网、鱼篓、鱼桶和一杆带有鱼篼的长竹竿等自产自销用的家当。谈妥了买鱼的品种、大小、价钱、数量之后,渔夫把鱼捉进长竹竿鱼篼,将竿子伸过来,把鱼倒进母亲递去的盛器里,顺手用篼接走付给的钞票,道声“谢谢”,调转船头,又箭般地飞逝而去。
这是我在栏杆桥边看到的最精彩一幕,平日都朝思暮想,希望天天都能有这一出。温州地区方言繁杂,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比如这卖鱼买鱼的“鱼”字,十公里外的瑞安城,说成“鱼儿”(yuer),第二声,儿化;到了栏杆桥,则要说第四声“鱼”(yu)。母亲很能入乡随俗,站在宅门口招呼、交易买鱼,满口是“鱼”,一回到屋里,马上就改口成“鱼儿”了。
除了买鱼外,还有一件跟栏杆桥沾边的事,也叫我永生难忘。一天,父亲突然想起要带我“出游”。夏日炎炎,人迹罕至,栏杆桥村宁静得只剩下白天树梢头的知了独唱,和晚间蝈蝈、蛐蛐、癞蛤蟆的合唱声,日复一日,有点单调乏味。见惯了瑞安城声色繁华的父亲,难耐寂寥,想换个不同环境走走。
那天下午,他唤来一只小船,父子俩在栏杆桥边下了船,半坐半躺到船舱的草席上。船夫“欸乃欸乃”地划着桨,小船在如网交织的河水中摇摇摆摆,曲里拐弯,朝着家乡瑞安地界划去,停在了大约是《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故里瑞安阁巷村和去林垟间的一座寺庙前头。
下船进得寺内,一位年长师父出来迎接道:“请问客人(客人)从哪里来?”父亲答道:“从四都来。”四都,是栏杆桥一带的旧名。在跟师父寒暄中间,父亲将一包“香烛钱”递给了师父。师父点上香烛,父亲拉我一起跪到佛案前头的蒲团上。合掌,叩头,跪拜,我第一次经历这套“戏法”,感到有趣而好笑。但见站在一旁的师父表情严肃,不敢笑出声来。向来不信教的父亲,这回有点异乎寻常,不仅见他第一回叩头拜佛,嘴里还念念有词。听不清他在念些什么,心里思忖,大概无非是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国泰平安、“逃反”快点结束……一类话语。时局动荡,漂泊外乡,有家难归,栏杆桥的幽雅娴静和佛门清净都难掩父亲不能淡定的心境,所以他要破例来此求神拜佛了。
表叔过桥
我家入住栏杆桥尤宅以来,几乎与世隔绝,从不见有人来过。但一天上午,家里的表叔突然到来。父亲感到很惊奇,问他怎么会知道我们住这里的。表叔说:“是叔公告诉的。我进村就见栏杆桥,哈,一过桥,就马上找到这里了。”原来我家赁居此地此宅,还是出于叔公的联络和安排。至于尤家与我“孙大昌”以前有何交集,一直是我不了解也不曾去打听的事。
表叔是我舅公儿子,名王炳华。舅公中年丧妻,无依无靠,就带着未成年的儿子炳华表叔和女儿素华表姑一起投靠、寄居我家,成了“孙大昌”大家庭中的成员。子女成家独立门户后,舅公本人依然留在我孙家,直至终老。像我们孙家这种叔父扶植侄儿,侄儿收留舅父终老的家庭伦理关系,在今人听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则是非常自然和常态的事。此时表叔年方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少,家里就派他做些外勤事儿。昨天叔公让他去林垟一带讨赊账,今天要回城,遵叔公吩咐,顺便拐到栏杆桥来看望我们。
表叔的年纪、性格都间于大人与我们小孩之间,我见他来特别的亲切和高兴。表叔平时很爱逗小孩玩,手头没有玩具,也会变出一套玩的花招来。比如去抓只小青蛙,用绳线系上肚皮,拴在竹竿上,到田边去诱吊田鸡。又比如更简单一点的,逮只红头苍蝇,背上贴上纸片,让它在地面“负重前行”。这些花招都会逗得我们小孩直乐。这天他在来的路途上,捕了一只“纺织娘”(草蜢),肚皮上给系上一根麻线,带到栏杆桥让我牵着玩。“纺织娘”长得长长绿绿的,腰身纤细,像个婀娜多姿的小姑娘。我提着线,让它在地面边跑边跳的,可把我乐坏了。
午饭过后,表叔就要动身回去,飘飘拂拂地过了桥,身影渐远,消失在对岸的拐角处……
表叔这匆匆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见他来栏杆桥了,因为不久他被日本兵抓走了。“七一三事变”期间,他在城里留守。日本兵从瑞安城撤退时,四处“抓担包”,抓了不少城内外的青壮年,荷枪实弹押着,逼他们随军搬运辎重,当牛做马,一路肩挑背负步行,吃尽苦头,还时时有丢命的危险。留在家中的炳华表叔不幸也被抓了去当“挑伕”。这一去,音信全无,全家人特别是年老的舅公,天天担惊受怕,茶饭不思。直到日兵退后两三个月,记得是天气也开始变凉的一天,表叔死里逃生被放还。这时,我们也搬离栏杆桥,回到瑞安家中。
表叔被抓时,阳历8月天还正热,上身只穿件汗衫。深秋回来时,上身添了件日本人“照顾”给他的一件紧巴巴长及肋骨的贴身衬衫。当他穿着蓝底、白条、粗布短衫,以一副又黑又瘦的面庞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惊喜、滑稽、酸楚、伤心等种种说不清楚的各种滋味涌上众人心头。舅公更是老泪纵横,说不出一句话来。而我想到的,还依然是那天表叔长衫飘飘拂过栏杆桥时的那番景象……
来源:温州日报
孙崇涛
(本文作者为著名温籍戏曲史家)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