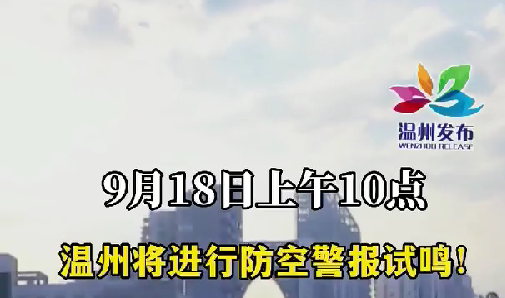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琐忆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

1981年8月《文学青年》创刊号(上图)与茅盾的题词(下图)。

1987年12月《文学青年》停刊号。
温州网讯 《文学青年》是温州市文联创办于1981年8月的文学月刊,适逢当时的“文艺春天”应运而生。我也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有幸在《文学青年》月刊当过编辑,责编过诗和散文。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文学老年矣,但回忆当年《文学青年》往事,亲近又很有滋味。
“四小名旦” 名家云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诗作《螺号》,责任编辑是刘崇善。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诗作打遍了上海的刊物,然后飞向全国。许许多多报刊编辑老师和朋友们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成就了一个爱诗写诗编诗的我。
我手头尚保存有《文学青年》的创刊号,刊名是茅盾题的。只一个多月后,他就驾鹤西归,这是先生病中唯一一个题签,也是先生在世的最后一个题签。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凡青年皆以文学青年为荣,《文学青年》的宗旨是“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这便理所当然地为全国的文学青年所青睐。刊物办起来之后,正好全国在宣传“山西刊大”,以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使全国广大学子为之向往。《文学青年》亦办起了函授,开始只想以文养文,第一期就招收到学员一万多人,函授规定有信必复;一期(半年)寄讲义两次、教材两本、函授版作品两册;每学期交作业3篇,有分片的老师专人负责看稿和评点;优秀学员报销车旅费来温管食宿参加笔会。如此种种,同时也把《文学青年》的种子撒向了全国。我手头还有几张优秀函授学员的名单,其中就有如今写小说出了名的北北(林岚)和刘继明,还有诗人谷未黄、黄殿琴、吕新、郑渭波、黄耘。
1983年下半年,《文学青年》开始由邮局订阅,发行全国。应该说,《文学青年》和《文学青年》函授是难兄难弟,没有《文学青年》,函授要想叫得响是会有一定困难的。同样,没有函授这支庞大的学员队伍,《文学青年》要想得以如此红火也并非易事一件,他们是一对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好伙伴。1984年编辑部工作小结中也说到邮局发行80000册,而且每月都往上涨,一直没有下降过。当时的文坛,将《萌芽》《青春》《丑小鸭》《文学青年》这四本文学刊物美称为“四小名旦”。
《文学青年》当年聘请的顾问班子也十分强大,有王安忆、邓刚、李杭育、张承志、叶辛、张抗抗、铁凝、孔捷生、贾平凹、陈建功、路遥、梁晓声、韩少功、徐刚、傅天林等,他们并不像如今有些刊物那样只挂个名不顾问事情,空装样子“拿架子”,都有顾有问,几乎都积极热诚,也为《文学青年》拉过关系写过稿,有的拨冗来出席笔会,有的来做过讲座,有的还为函授学员批改作业,进行点评……可以说,一个个是《文学青年》的有功之臣。《文学青年》发过两个“短小说专号”及北京、湖北、浙江等三个“地方专辑”,群起响应的都是当时重量级的作家。全国活跃和有名的校园诗人也纷纷向我们投稿,可见当年《文学青年》的影响力与凝聚力是何等之大!
《文学青年》是1987年在所谓“批判精神污染”的风浪之中被停刊的,用“文坛震惊”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停刊亦并不为过。我手头除了保存创刊号外,还保存着刊登编辑部《告别词》的1987年12月、总第68期的最后一期《文学青年》。我无意回答有哪些人发过处女作,这些人中间后来在诗坛上成名的都是谁,更何况当年编诗是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应尽之责,但每一期上的诗歌版面占7个页码这是雷打不动的,其中4个页码可以编发4至6人的组诗;3个页码是短诗专辑,以每人1首计,可以编发12人至16人。以此推算,大概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人次了。不少诗歌后面的尾饰,都是我自己画的。这里,我要重点指出的是,当时内蒙古出版有一本《诗选刊》,经常选编《文学青年》上的诗作,除了由我每期寄荐之外,亦不乏我国著名诗人主动推荐被选用的。我敢夸口说,当年,几乎全国著名的和不著名的青年诗人都给《文学青年》寄过诗作并发表。
印象特别深的倒是北京的老诗人顾工(顾城之父),曾经几次寄来诗稿,因为他已经不属青年之列,被我复函致谢并退稿致歉处之。编最后一期《文学青年》时,许是我想尽可能多发几位诗人的诗作,那一期的诗歌作者有李曙白、殷红、杨川庆、王中朝、李祖星、曲庆玮、晓梅、张东辉、卫世平、阮文生、魏守星、盘妙彬、作二、赵焕明、陈伊丽、柯平、秦安江、李清晨、程蔚东、温柔等20人之多。而最后一首以“温柔”署名的《留给恋人的歌》乃我所写,也算是作为该刊诗歌编辑的“告别词”而已。
前辈提携 因编交友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诗歌编辑,我努力过、尽心过、快乐过,也为停刊而无奈过、义愤过、痛苦过。而投稿或在刊物上选编用过诗作的朋友们所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我谢谢你们。有两件事情,亦不妨说一说:一是当年部队诗人叶文福发表《将军,你不能那样做》之后,我听说他在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便主动去信向他约稿在《文学青年》上编用。有一年九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驻校诗人的文成王国侧(慕白)小兄打来的手机。说自己在与一班诗人朋友在吃夜宵,大家都要与我说说话。我觉得国侧当时已经醉了,他连连地说自己没醉,把手机递给了商震,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与我通话,有十几位友人,最后通话的是著名诗人洪烛。洪烛说,自己当年如果不是我在《文学青年》上发了他的诗,他或许就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又说,如今在北京生活得很好,欢迎我到北京时去他家作客,一定请我喝酒……洪烛的话着实使我感动了很久很久,感到很温暖。我想,这辈子爱上诗歌爱对了,竟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还没有忘记我。
我能当上《文学青年》诗歌编辑,必须感谢三位令我敬重的前辈。《文学青年》创刊之时,也许鉴于我在全国的报刊上已经发表过不少的诗作,《文学青年》创始人、小说家何琼玮提名并推荐我当上了诗编。他曾经被错打成“右派”,为了养家糊口,当过飞机牌供销员,改正之后落实到市文化局。《文学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舒婷诗作《丽帆》,并非是本人投稿,是何琼玮通过他的友人、福建作家曾毓秋搞到的一本油印诗集,交给我之后选编的。第二位要感谢的是吴军,他当时担任市文联主席。“文革”时期,我曾经参与过对他的批判,当时很怕他会记恨而将我扫地出门。谁知他却以宽阔的襟怀不计前嫌,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这世上哪有不犯过错误的人,知错改了就好,继续好好地干。更让我感动的是,批判“精神污染”之时,有人要拿我的诗作《我是骆驼》开刀。吴军说:“这首诗哪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批的?!”硬是为我顶了过去。这是庄南坡事后告诉我的。第三位就是庄南坡,一位被错划为“右派”而平反的老编辑,亦师亦友,担任了《文学青年》副主编。我能当《文学青年》的诗歌编辑,可以说是在游泳中学游泳,是一生难忘的学习机会。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划诗歌版面,他说:“编辑要和作者交朋友,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更是他,以身教言传教会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应有的好作风。
当年,我在浙江与青年诗人柯平、伊甸、陈云其等交上了朋友,结成了“狐朋狗党”。年龄上我是老大,写诗他们都比我强,彼此亲密往来,很是让我学到了不少写诗的本领。说一件趣事:1985年8月,我与柯平等相约一起去西天目山玩,在车上遇见了四位活泼可爱的杭州少女,我们打趣地对她们说:“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的食宿是可以公家报销的哩!”那时候,还并没有如今流行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之说,旅游也都是自掏腰包,一句戏言竟让这四位天真的少女信以为真,真的就很乐意地跟我们一起住进了西天目山某旅社。我们在绿荫蔽日、岩石突兀的涧水边游玩时,柯平故意惊叫“有蛇,有蛇!”竟使其中的一位少女受惊吓而掉进水潭之中,于是,彼此有了一场水战,弄得大家都浑身被水泼透。好在还是夏天,各自在隐蔽处把衣服拧干了又毅然登山。下山的时候,自然引起邂逅的旅人的惊愕目光,“山顶上下了一阵雷阵雨……”这是我们统一口径的解答,然后抛下一串神秘的欢笑声下山而去。这四位少女的食宿自然由我们诗人包了下来。第二天傍晚,送他们去车站上车回杭州的时候,大家都似乎有些依依难舍。那时,我才说了实话:“我们也是自费来游的三个诗人,能和你们一起玩,很开心。多写一点稿子,稿费拿回来,就足够我们这次一起玩的开销了……”事情还真是这样,我们后来都写了一首《三个男人和四个少女及旅途中一支短暂的歌子》的同题诗,都发表了。写诗,有时还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还有北京的初军,当年是一家大厂的宣传部干部,是个爱诗狂,也是个经常向《文学青年》投稿的人。他的字迹特别端正,让我很为他对诗的虔诚和执着而感动。我是每信必复,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他也有诗作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但我在《文学青年》上却从来没选发他的诗,总觉得欠火候。我写信对他说:“你是否可以试试写报告文学,把你写诗的激情融化到报告文学中去,也许你会有更大的成功……”后来,他写报告文学果然拿了全国大奖,还加入了中国作协。我俩曾经合作主编过《东部诗丛》,至今还有密切的来往。
江西诗人郑渭波、纪辉剑和膝云,都曾经是《文学青年》的函授学员,后来都成了江西的著名诗人。有一年,我去龙虎山参加一个诗会,膝云也去了,能见面就已经是十分开心的事情。会后,膝云用他的小车邀请我一起去了上饶,与郑渭波、纪辉剑上三清山,有过一回难忘的欢聚。从此,我与他们均有了经常的联系,后来,我为膝云的诗集《三清之旅》写过诗评。只可惜膝云后来因车祸而英年早逝,纪辉剑亦被病魔缠身而提前离开了他的电视事业。命也,运也。每想起这些,就会使我心情黯然。再后来,江西上饶组团来温州党校学习,郑渭波也来了。临别之际,我请他给纪辉剑带去几百元钱买点营养品,数目虽小,也是表达一种心意而已。郑渭波至今跟我常联系,什么时候又发表了诗作,什么时候诗作又获了大奖……都会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儿子绿周结婚时,光是诗人出席酒宴的就有30余人之多,均来自温州和全省各地。至今,我与全国的许多诗人和文学朋友仍然有书信联络,收到朋友们的来信,是我的盛大节日,给朋友们写信,是我的快乐。
当年我与全国青年诗人们广泛、不断的交往中,使我学习到了许多知识并丰富了我的人生。我现在依然一往情深在关注着诗坛和我熟识的、不熟悉的诗人们,因为我的爱诗之心不变。如当年东北的校园诗人、如今著名诗人潘洗尘,在他参与“诗人宣言”并创办《星星》上半月刊期间,我俩又恢复了联系至今,每期寄赠我都会认真阅读,以为这是一册重在诗歌理论和评论的好刊物。当然,我还有许许多多至今仍与我保持往来的当年的诗人朋友,至今凡有诗集问世均有寄赠于我。诗缘与友情,两者皆珍惜。
我一直以为,写诗的人都必须豁达正直热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我国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兄也曾以“身心豁达”四字书赠于我,被我视为墨宝珍藏。著名汉语国际诗人洛夫曾经提出过“继承传统,拥抱现代,做一个历史见证人的中国的诗人”的主张,我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我七十寿辰时书赠我一纸书法:“生命的价值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心中有诗有爱,刹那即是永恒。”至今还一直挂在我以“蜗牛居”为名写作的斗室之中常读常新。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
——琐忆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
作者:叶坪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
相关新闻
为你推荐
-

聚焦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闻09-16
-

新学期劳动课怎么上?温州众小学“各显神通”
社会09-16
-

揪心!高温干旱天气“作祟” 永嘉板栗大幅减产
社会09-16
-

金茂府业主违约封窗 物业:若不复原,将司法维权
社会09-16
-

别看文具“不起眼” 小心也会有“刺客”
社会09-16
-

现场直击:一个灯次,四五辆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社会09-16
-

唤醒东沙港 洞头即将打造“渔港综合体”
社会09-16
-

从代加工向自主创新转变 品牌为帆向蓝海
经济09-16
-

花期调控见成效 紫薇二度怒放
社会09-16
-

省运会空手道比赛激烈对决 温州健儿勇夺2金2银6铜
科教文体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