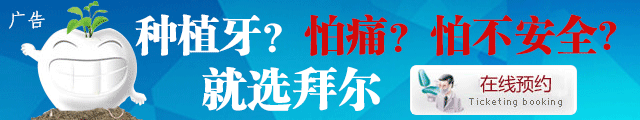著名作家戈悟觉深情追忆发小叶永烈
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5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叶永烈先生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以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而成名,以“四人帮兴亡”等长篇纪实文学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而今驾鹤西去,令人痛惜缅怀。法制洋葱头公号今天特刊发戈悟觉先生的追忆文章《我和阿烈》,以寄托对叶永烈先生的共同崇敬和哀思。
戈悟觉先生也是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建设,在宁夏工作了几十年,担任过自治区作协副主席,系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夏天的经历》等。戈悟觉先生与叶永烈先生不仅同为温州人,同为北大校友,同为著名作家,而且两家系世交,同住温州铁井栏,自小一起长大,彼此间情义长达七八十年。戈悟觉先生追忆发小叶永烈先生,笔触不同寻常,相信各位读后,也定会别有一番感慨上心头。
我和阿烈
戈悟觉
喊叶永烈阿烈,不合适,乱了伦次。我喊他哥阿叔,喊他令尊叶志超先生阿公;阿烈喊我爸为阿哥。那怎么称呼?他小我3岁,在北京大学又是我学弟。我喊他叔叔喊不出口,他也不好意思正正经经答应。中国人的称呼太繁琐,外国读者看不下《红楼梦》原因之一是称谓太纠结。

图为两家人合影,前排左三为叶永烈,前排右一为戈悟觉
我们通家之好。同是乐清人。他父亲是我父亲的恩师。我父16岁从磐石到温州学生意,阿公收留、提携。阿公是咸孚钱庄总经理,我父后来是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两家同住一层楼,同饮一井水(铁井栏),同吃一桌饭。直至1945年。我们一起躲避日寇逃难永嘉鲤溪。阿公有过军旅生涯,我家先回温州了,另租房子。但依旧是不是亲戚胜似亲戚。
只记得阿烈4岁时的一件事:一天早晨,突然发现阿烈不见了。楼上楼下、门里门外找了个遍,不见踪影,两家人惊惶失措。一二个小时后才“活捉”了,原来睡觉不老实掉到床下被蚊帐裹住了,悬空挂着,他还睡他的。长大了我打趣说:“你干什么都这么专注投入呀。”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1955年我考取北大中文系,给阿烈写了封“热情四溢”(阿烈语)的信。介绍校园的美,教授的多,迎新活动的多采。他回信:“非常非常向往!”1957年他中学毕业了,报考志愿想要填中文系新闻专业。我当年考取中文系不分专业,到校后几个月才分开,立志研究的去汉语言文学,去新闻专业的多半怀揣作家梦,因为苏联作家百分之八十来自记者。我如实相告,我们班里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来自调干和留苏预备班(苏联拒收),中学直接考上的才二十多人。没料到这封信把他吓着了。他考上北大化学系。
命运作弄人。这关键时刻的选择,是祸?是福?现在可以站在终点回望了。

图为叶永烈与戈悟觉在上海生活合影,二排右二为叶永烈,三排右一为戈悟觉
如果不上化学系,大概率不会有《十万个为什么》的编纂和书写了,当年出版社是去北大化学系组稿;中概率不会有科普和科幻作品的书写了。小概率是会免除“不务正业”、“名利思想”的屈辱、磨难。1966年他对我说,他至今未转正!大学毕业通常第二年便转正,何况他是北大毕业,化学系六年制毕业。他15年蜗居在上海边缘的12平米房子里,一代、二代有时三代人(阿婆去照料两个儿子)同居。我去看望他,从天花板上传来他儿子叶舟的声音:“爸爸,谁来了?”他把房间隔成二层。直到1979年,阿烈获中国科协、文化部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和1000元奖金,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给上海写信,才获得40平米的两居室。他太太杨惠芬回忆写:“搬到新居后,欢乐的气氛洋溢整个房间,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阿烈是出色记者的料。他机敏,闻风而动,审时度势;对时事永远充满好奇心,又敏于行,不知疲倦地游走、追寻。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拥有几百万、几千万读者。我时常把阿烈和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比较。她是第4位纪实文学获诺奖的作家。她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转型、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阿烈得天独厚生活在中国,10年浩劫,改革开放,在揭示人性、真相探索,以及十几忆人的命运期待,都是有震撼世界的书写价值。如假以时日,改变思维习惯、写作方式和风格,他完全可以与阿烈克谢耶维奇为伍,也许会是第5位。

阿烈在北大住31斋,我在30斋,比邻而居,但不多来往。是那种相见也无事,不来忽忆君的关系。偶尔相约看场电影。他入学那一年,北大反右风起云涌。阿公在温州也受到冲击,打成什么分子。但没有告诉阿烈。我接家里来信,便约他“聊聊”。我们没有去风景旖旎的校园未名湖,就坐在楼前的青石台阶上。他很镇定,只说一句:“怪不得许久没有来信。”他平日就话不多,我也找不到开导的话。我们并肩坐着,我一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沉默,只是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直到两座楼的灯光熄灭了。我和他站起来,两个拳头碰了一下,说:“不怕。睡个好觉!”
第二年,反右斗争后遗症,有人提出新闻专业要提升政治素质,将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年后,新闻专业又回归北大)我和他分手了,通信联系。毕业前夕,我约他同去参观还没完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是当下全国最大的体育场。我是向北京告别,向体育告别。生活还需延续。我在寻找这种感觉。突然看到体育场的介绍:沿着各个座位走一趟,一个人一生一世才能走完。我们又喟叹唏嘘一番。阿烈说:“人生就是这么短!若是人生道路看得这么清楚也好。”
阿婆说:“阿烈执显执。”(温州话)
这是不作寻常事的自信和坚持。比如,他自制绿墨水,用钢笔写绿字。我以为他姓叶,玩笑。没想到他坚持好几年,让人“忍无可忍”了。比如,他忽然对冲洗照片感兴趣,要去我好多底片。自己配料。相片带浅蓝色,相纸又不正规发软。但他乐此不疲,还要我找朋友借底片;他的摄影技术一般,留影自娱自乐不妨,但要发表,还出书。我劝他,不听。比如,他固执地反对体育锻炼,说最好的运动是睡觉。这观点和北大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不谋而合,我也不和他争论了……
我回到家乡工作,和阿烈的接触又多起来。发现他越出名,采访过历史性人物越多,性格也随和了,豁达了,越发谦和低调。

图为叶永烈和戈悟觉合影
我来温州不久,应温州日报之邀开“名家随笔”专栏。开篇我约阿烈写。他很痛快答应,把他为香港回归而写的稿件给我们首发。2003年10月,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市电视台约我作访谈节目。我推荐和阿烈对话。阿烈中止在北京的工作专程来温。电视台没人去车站接,没有安排食宿,也没有向阿烈征求意见。我觉得太怠慢。不悦。正向他抱怨和致歉,他却坐在我身边睡着了。阿烈没有架子,温州的活动,无论讲学,写稿,甚至一般的庆典,一叫就到;一些素未晤面、不相干的人去信,只要有可能也是一一回复或赠书。我问:“累不累?”他说:“别人一番心意。累也罢。”
5月15日中午,我得知阿烈去世,呆住了。我知道他近几年健康出问题,去电话问,他总说没什么事,最常说的话:“快出院了。”这几天,我一直为此时写追忆的文字是否合适。他不作兴凑热闹,我们常取笑他人“应景”;他也看淡生死。
1968年3月22日早晨,文革中我从温州回宁夏路经上海,他到码头接我。我说:“阿公身体还好,来前我去过。”这是例行的宽慰话。他说:“昨天夜里病逝了。我马上要回去奔丧。”我吃一惊,也有点尴尬。我两天前去向阿公辞行时,他还能坐起,送我抄家时唯一遗留的传家宝——青田石白桃枝叶笔洗。笔洗这时分外珍贵了。阿公爱诗词,善书法,一直对我家、对我很好。倒是阿烈宽慰我了,背陶渊明的诗:“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他说这是他的生死观。这两句诗,还有前面的两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多次背诵。回到我借住的小姑家,急忙打开箱子检视笔洗。笔洗是里三层外三层毛衣、棉毛裤包裹,小小翼翼打开,已粉碎。只留下一个完整的白桃。我坐海轮到上海的,粉碎的时间大约也在昨天。
“亲戚或余悲”……
我书柜有好多阿烈的赠书,包括早期的《碳的一家》,还有阿烈用心阅读过的书,如划着绿线条的《古文观止》。最新的书是他的自传《华丽转身》。70多万字。2018年5月1日。题字:“阿觉存念:何当共剪西窗烛”。我回复:“却话瓯江夜雨时。”

阿烈,不管你高兴不高兴,这篇小文我还是写了。不写吃不香、睡不安。我想你会笑一笑的。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