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今日凌晨辞世 享年105岁TAG杨绛 辞世

杨绛 2012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据悉,2012年3月26日,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来看望时,杨绛先生曾提出三要求:
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
二、不受奠仪
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杨绛生平:一个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TAG杨绛 生平

晚年杨绛
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与钱钟书 他心中“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TAG杨绛 钱钟书

1981年与钱钟书、钱瑗摄于三里河家中
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风华正茂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 (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在钱钟书离去之后的那些年TAG杨绛 钱钟书遗稿

杨绛先生即便是在近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尤其是整理出版了钱钟书数十部遗著。这对为人治学皆堪称完美的世纪老人,可谓功德圆满。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在缠绵病榻一年之后离开人世。而前一年,这对夫妇唯一的女儿钱媛因病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容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
此时杨绛已是87岁高龄。世人将看到一个更深居简出的作家、学者、钱钟书遗稿的忠实整理者。
2001年9月,杨绛先生以全家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信托协议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这一名字与钱锺书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当年杨绛为奖学金捐助现金72万元,到2011年,已是929万元。
杨绛一力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作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
2003年,92岁的杨绛重新提笔,在该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书中回忆了她与钱锺书一路走来的时光,以及丈夫与女儿生前最后一段日子。
杨绛:“什么家也不是,我是一个无名小卒”TAG杨绛 访谈
虽然杨绛对写作特别是小说的写作一往情深、始终不渝,虽然她其实早在1953年,即已加入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但她却仍是一以贯之、斩钉截铁地屡屡宣称,自己绝不是什么作家:
刘梅竹:您和当代作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杨绛:他们是作家,我不是。
尽管杨绛称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学多面手——不惟在散文、戏剧和小说诸方面都能有所成就,连文学翻译也能做到独树一帜、蔚成一家,尽管她的创作成果虽并不如何丰硕却早已为世人所瞩目,尽管连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主席铁凝也以将她引为忘年交为荣,但她却还是依然故我地一直认定,自己只不过是在从事毫无功利性的业余写作而已,最多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家:
刘梅竹:您是什么?学者,作家?
杨绛:什么家都不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也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不求加入他们的行列。

杨绛与钱钟书 对杨绛的这样一种为文态度,有的论者也曾有过比较翔实、到位的归纳与总结:
“……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白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一文里,杨绛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主要作品TAG代表作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杨绛先生以她92岁的那年划分了前后两个创作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她的写作服膺于天赋,并且因为顾及丈夫与家庭而在历史洪流中暂告段落。在后一个时期,她用余生喘息的时间整理家庭钱钟书的著作,并让自己更重要的心性文字问世。

杨绛先生是一名伟大的遗孀,她不只是复活了钱钟书的遗著,更是把他作为文人的生涯重演了一次。对于爱女钱瑗,同样如是,杨绛先生用独特的散文保留了一家三口可以达到的幸福生活。她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因为她拥有过比一个世纪还要悠久的美丽世界。

一部《堂吉诃德》译作足以让杨绛映照后来,相较而言,她那追忆丈夫与女儿的散文巨著,则象征了中国散文史上一次别有深意的崛起。她的散文,仿佛是从天而降,仿佛有果无因,但事实上只是她这辈子生活的副产品,是一直英俊的钱钟书,一直还是孩童的钱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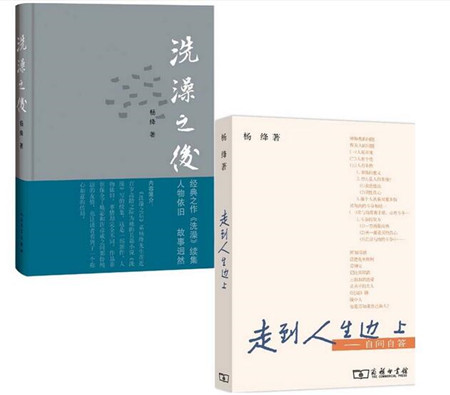
在丈夫去世五年后,杨绛先生重新拿起了笔,用记忆来替代对丈夫、对女儿的爱,并且在纸上复活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存在。杨绛先生用她最擅长的部分,履行了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那份“无论生死”都要去爱的契约,而世人尤其从这部分中获得教益。
作品选读:《读书苦乐》TAG
文|杨绛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
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
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
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
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潘涌燚
潘涌燚 张湉
张湉 鲍苗苗
鲍苗苗 诸葛之伊
诸葛之伊 陆珊珊
陆珊珊 杨丽
杨丽